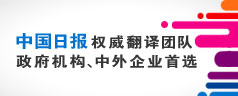在美國商界和政界,工會長期以來都是一支強大的力量。但是最近幾十年來,隨著會員隊伍的萎縮,工會的影響力一直在急劇衰退。除了工會尚能保持令人敬畏地位的少數幾個行業——其中就包括航空業,最近,全美航空公司(US Airways)與美國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的合并,就得到了來自美國工會界的支持和促進——之外,其他行業工會的力量和影響力的衰退可能還會繼續。“在大部分工作場所,工會的力量和影響力已經衰退到了無足輕重的地步。”沃頓商學院人力資源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主任、管理學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談到。然而,工會沒有專注于擴張,相反,他們只是試圖將每年喪失的領地減少到最低限度,他表示,“無論在哪個方面,他們在繼續保留契約安排的權利方面都步履維艱。”
工會會員的統計數字也證明了這一趨勢。美國勞動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統計數字顯示,2011年,美國有11.8%的工薪工作者——也就是1,480萬人——是工會會員,這一數字低于1983年1,770萬人——占工薪工作者20.1%——的水平。但是,這還是包括了公共部門會員隊伍在內的數字。而在私營部門,工會會員數量的減少則更為顯著,只有6.9%——即720萬人——是工會會員,比20世紀50年的水平減少了大約三分之一。“工會的聲音已經不能被視為一個重要群體的聲音了。”沃頓學院法律研究與商業道德教授詹尼斯·貝爾雷斯(Janice Bellace)談到。“即便他們的觀點得到了大多數工人的支持,人們也很容易認為這些人是個小群體,在其中擁有特殊利益。”
工會力量的衰減對美國的勞動力市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馬修·比德維爾(Matthew Bidwell)進行的研究表明,工會化水平的降低,與員工任期的縮短密切相關,而員工任期的縮短則造成了更高的人員更替率。至于說這種變化對員工來說會產生正面效益(員工通過轉換工作來尋求更好的機會)還是負面作用(長期工作的員工在現有工作單位升職的機會更少)尚不清楚。但是,無論員工為此會受到怎樣的影響,這一趨勢對于企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其中就包括員工的培訓和聘用。
其他研究表明,工會的衰退和收入差距的擴大有關。哈佛大學和華盛頓大學去年發表的研究成果顯示,在美國,從1973年到2007年,私營部門工會會員數量的減少,是導致同期收入不平等惡化的的重要原因。
“工會對非工會員工的收入也有影響,因為有些雇主此前會擔心工會化的壓力,所以,他們將員工薪水提高到了與工會要求相匹配的水平。”華盛頓大學的社會學教授、該項研究的合作者杰克·羅森菲爾德(Jake Rosenfeld)談到。“工會在工作場所建立了人們認為恰當而且公平的工資標準,而非工會員工則能從中受益。就解決收入不平等的問題而言,很難想象除了生氣勃勃的勞工運動以外還有其他什么途徑。”
此外,工會的衰退也產生了政治影響。當然,工會依然擁有政治力量。“從絕對數量來看,依然有很多人是工會會員,所以,他們仍然擁有很強的勢力。”卡普利談到。“他們可以發動選民登記動員,同時,他們也可以幫助人們退出選舉——所以說,他們依然是選舉中的一股力量。”但是,羅森菲爾德也指出,私營部門工會會員的減少對投票模式的影響則大得多。他在2010年發表的研究成果顯示,私營部門工會會員的投票預測概率,比非工會會員的類似員工高6.7%。從投票人數的增長來看,私營部門工會對員工投票可能性的推動力度,要遠遠強于公共部門工會對會員的推動。他還指出,隨著工會會員數量的減少,美國工人階層對政治過程的參與度也可能會同時降低。“就(政治捐款)而言,工會永遠無法與公司匹敵,所以,他們會在人員的數量上與公司展開競爭。”羅森菲爾德談到,“但這種現象已經日漸式微了。”
另外,還有證據表明,工會會增加工人理解和充分利用自己在現行法律中享受的那些權利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工會會員可能聽說過而且也清楚《家庭醫療休假法》(Family Medical Leave Act,簡稱FMLA)賦予自己的權利都是什么,所以,他們更可能參與失業保險計劃,這可能就是因為工會給他們提供過信息。”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卡爾森管理學院(Carlso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約翰·巴德(John Budd)教授談到。“工會確實讓勞動法更具效力了。”
衰退的原因
雖然(工會衰退的)其它影響很難評估,但這些影響的重要性并不小。貝爾雷斯認為,工會的衰退同樣也影響到了工人在立法程序中如何被代表的問題。“看看對工人一直非常重要的法規,你往往會發現,這些法規的出臺都是由工會推動的。”她談到,“1974年的《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簡稱ERISA)——該法規為員工賦予了享受既定退休金的權利,并對退休金有明確的規定,其中包括雇主如何向退休基金投資等規定——就是由工會促成的,幾乎沒有其他機構的介入。因吉爾伯特(Gilbert)案例于1977年出臺的《懷孕歧視法案》(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就是由美國電氣、無線電和機械工人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Electrical 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簡稱IUE)提出并將其提交到最高法院的。”雖然除了工會以外還有其他一些政治黨派,“但我們并沒有聽到它們為普通工人階層發聲。”貝爾雷斯明確指出。
工會的擁護者堅稱,這樣的現實最終會讓工會化運動復活。“允許首席執行官的薪酬水平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減少對金融部門的監管,以不平衡的方式開展貿易,收入不平等愈演愈烈——所有這些問題讓99%的人懷有挫敗感。”杰夫·豪澤(Jeff Hauser)指出,他目前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負責2012年選舉的政治媒體工作。“我認為,人們越發認識到了這種失敗,并對改變這一現狀有了越來越多的開放意識,此外,工人們也越發意識到了聯合起來的必要性。”
但是,改變工會變化的軌道卻是個艱巨任務。很多人認為,職業航空交通管制人員組織(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PATCO)1981年舉行的罷工是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羅納德·里根總統解雇了大約1.1萬名無視其復工命令的航空交通管制人員。雖然那是一場聯邦政府員工舉行的罷工,不過里根的舉措也給私營部門雇主對工會采取強硬立場壯了膽。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約瑟夫·麥克卡丁(Joseph McCartin)認為,其結果就是,工會組織罷工的數量顯著減少了,2002年,參加罷工的員工數量,降低到了只有1952年六十分之一的水平。“在生產率和利潤增長帶來的好處中,員工并沒有確保自己能享有一定份額的手段,在我看來,他們把原因歸咎為不斷擴展的經濟波動。”他指出。
最近,威斯康星和其他州的公共部門工會,遭到了某些政界人士越來越多的攻擊,這些政客正在力爭讓限制工會集體談判權的法規獲準通過,事實上,這些法規將剝奪工會在工資、工齡、退休金、醫療保健以及與工作相關的其他問題上的談判權。
卡普利談到,公司阻礙工會化的激進行動得到了法規變化的支持。“負責監督有關工會法規執行的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是由政治任命者(political appointee)管理的,而近年來的規定也變得越來越有益于雇主的利益了。”卡普利談到。“控制選舉過程如何運作的規定,使公司管理層對抗工會變得更容易了,而對違反這一法規的懲罰則微不足道的。如果你解雇了某個支持工會的員工,修正這樣的錯誤要幾年的時間,可那時候,選舉早就完成了。通常情況下,補救措施不過只是恢復那些(已被解雇的)員工的權利而已,但是,因為這些人的處境會極為悲慘,所以,他們根本無法堅持下去。”
貝爾雷斯指出,美國制造業——一度是工會非常集中的部門——的衰落,以及公司管理層對工會化的對抗,也是工會衰退的重要因素。但是,她也談到,美國出臺的法律也對這一衰退起到了重要作用。“1935年獲準通過的《國家勞動關系法》(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是個陳舊的而且很有局限性的法令。”貝爾雷斯談到。“這個法令將(想要把組織工會的個人)推向高度危險的境地。此外,這個法令還為工會化設定了選舉機制,這是不同尋常的。在大多數國家,都不存在這種規定。這個機制將全體員工的一半排除在外——舉例來說,只要被視為管理者或經理人,都不得加入工會。而人們對這一機制定義的解讀極為寬泛。另外,公共部門的員工、農業工人以及家庭團體也不包括在內。”貝爾雷斯還補充談到,與此同時,美國對員工權利的認識完全不同于其他很多國家。“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很多權利都止于工作場所的大門——他們更愿意接受雇主的權威。” 貝爾雷斯談到。“這一點與其他發達國家的情況大相徑庭。”
不過,卡普利認為,工會的失策也是造成它們目前困境的一個因素。“工會也面臨著所有組織都面臨的兩難處境:你是將自己的資源用于招募新會員呢,還是用于照顧好既有的會員呢?”卡普利談到,“20世紀70和80年代,工會在組織新會員方面并沒有花費多少時間。”
前景堪憂
當然,在某些市場領域,工會依然擁有強大的力量。在汽車、建筑和航空等行業,工會依舊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們來看看美國航空公司的例子,該公司申請破產保護以后曾試圖重組。該公司的競爭對手全美航空公司4月中旬宣布,與另外兩家航空公司合并的努力,得到了美國三個工會的支持。一樁交易得到工會的支持很重要——他們能降低美國航空公司保持獨立的可能性——因為工會在監督組織重組的債權人委員會擁有席位。
但是,即便在工會依然是一支有生力量的行業,工會的前景也頗具挑戰性。舉例來說,在汽車行業,工會未能滲入本田汽車公司(Honda)和豐田汽車公司(Toyota)等外國汽車制造商設在美國的企業。雖然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簡稱UAW)主席鮑勃·金(Bob King)曾說到,工會要選擇一家裝配廠,將其當作組織工會的目標,但在2011年年底,迫于形勢又退縮了。“我們并不是要宣布一個目標,我們不想挑起戰爭。”金對《汽車新聞》(Automotive News)談到。雖然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依然要在裝配廠成立工會,但其息事寧人的行動卻表明,如果汽車制造商極力抗爭,那么,在那些工廠成立工會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雇主則把工會的衰落當成了很好的消息。但是,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伊萬·巴蘭科(Iwan Barankay)認為,工會的衰退對公司也是一個不利因素。巴蘭科談到,雖然與工會談判“可能并不令人愉快,但是,這是一個大家都明了的過程。公司高管很了解的自己的對手,他們可以據此計算罷工讓公司付出的代價。”然而,員工現在有了表達不滿的新工具,這要感謝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現在,人們可以非常高效而且強有力地將自己組織起來。”巴蘭科指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公司雇員可以和其他企業的工人和消費者聯合起來向雇主施加巨大壓力的時代。他們之間的聯系可以‘像病毒一樣擴散’,他們可以和消費者結成同盟,從而,會使一家公司出乎預料地陷入財務困境。這遠比與一個工會面對面地談判更難以應付。”
事實上,巴德也認為,如果工會的組織過程更具創造力的話,他們依然可以重獲契機。他指出,今天的工人在思想上已經更獨立了,他們認為,并沒有什么適用于全體員工的萬全之策。他談到了娛樂業和體育業工會的成功案例,這些工會就是靈活的勞工組織。在這些行業中,“工會并不要就每個人的薪金與雇主展開談判,”巴德談到,“他們談判的是一個框架:某種最低比率、通用的醫療保健計劃以及談判個人聘用合同的程序等。個人的背后依然有工會這個資源。這種類型的工人運動對那些尋求自治權的員工來說更為有利。”
然而,盡管有某些成功的模式,但沃頓商學院的卡普利等觀察人士并不認為工會運動會復蘇。“除非美國的政治氣候發生重大的改變,否則,很難想象這一領域會發生什么轉變。”
本文由Wharton知識在線授權使用,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原文鏈接: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index.cfm?fa=article&articleid=2596&languageid=1
(來源:沃頓知識在線 編輯:旭燕)